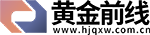加快推進數據產權明晰:筑牢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基石
-
 新華網
新華網 -
 2025-08-27 16:24:54
2025-08-27 16:24:54
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。數據是繼土地、勞動力、資本、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,其戰略價值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數據要素的高效配置,本質上依賴于清晰的產權界定——只有明確數據歸誰所有、如何使用、收益如何分配,才能激發數據生產、流通、應用的全鏈條活力,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。當前,我國數據產權制度仍處于探索階段,“數據二十條”雖初步構建了“三權分置”框架,但數據所有權的模糊性、數據收益分配的失衡性等問題,已成為制約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瓶頸。下面從產權明晰的現實緊迫性、理論支撐與國際經驗、實踐路徑三個方面,闡釋數據產權制度建設對高質量發展的意義。
產權界定滯后: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現實梗阻
數據要素的特殊性在于其非稀缺性、虛擬性、非耗竭性、非排他性與可復制性,這使得其產權界定遠比傳統生產要素復雜。2022年出臺的《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》(即“數據二十條”)首次提出數據資源持有權、數據加工使用權、數據產品經營權“三權分置”的制度設計,為數據流通提供了初步規則。但該框架回避了最核心的所有權問題,導致數據要素市場呈現“源頭模糊、中游混亂、下游失衡”的結構性矛盾。
個人數據作為公共數據與企業數據的“源頭活水”,其所有權歸屬是整個數據產權體系的邏輯起點。大量公共數據來源于個人行為記錄(如水電繳費、交通出行等),企業數據中用戶生成內容(UGC)占比也較高。這些數據在收集過程中,往往通過“格式條款”被平臺無償占有——用戶點擊“同意”按鈕的瞬間,便喪失了對自身數據的控制權。一些互聯網平臺的用戶協議中明確規定:“用戶同意將所有數據永久、免費、不可撤銷地授權給平臺使用”,這種不平等的權利讓渡,形成了數據要素分配中的強者更強弱者越弱的“馬太效應”。個人數據收益占比與數據生產者的貢獻嚴重不匹配。
公共數據領域的產權模糊問題更為突出。政府部門通過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務等途徑收集的海量數據,其所有權歸屬長期缺乏法律界定。有的地方交通部門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智慧停車系統,基于市民出行數據產生收益,但數據貢獻者未獲得任何分成;有的省級電力公司利用用戶用電數據構建負荷預測模型,被第三方企業收購,而眾多用戶對此毫不知情。這種“數據采集免費化、數據應用商業化、收益分配壟斷化”的模式,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,更抑制了公眾參與數字經濟的積極性。不少受訪者因擔心數據被濫用而拒絕提供非必要信息。當衡陽18億拍賣政務數據、重慶市涪陵區1.08億轉讓數字資產等重磅消息闖入公眾視野時,卻都無一例外遭遇迅速叫停的命運,宛如一記記重錘,敲打著數據產權敏感的神經,也引發了無數疑問與沉思。叫停主要因素就是數據產權不明晰,假若公共數據中明確哪些數據歸政府所有,哪些數據歸企業所有,哪些數據歸個人所有。合法確定數據所有權,取得的收入根據所有權返給數據貢獻者。正如筆者采訪某政府分管副市長時他說:很多地方政府財政十分緊張,卻守著大量值錢的公共數據不敢變現,主要原因就是數據產權不清。導致數據供給的“自愿性短缺”。
企業數據的產權邊界同樣存在爭議。平臺企業通過算法對個人數據進行加工形成的數據產品,其權利性質如何界定?曾有電商平臺與數據服務商的侵權糾紛,法院雖認定服務商非法爬取數據構成侵權,但未明確平臺對這些數據的權利基礎。這種司法實踐中的模糊性,使得企業不敢投入巨資進行數據開發,很多企業因顧慮產權保護不足而不愿開放核心數據參與跨行業流通。
產權不明晰導致的“公地悲劇”正在顯現:一方面,數據持有者因缺乏排他性權利而不愿投入資源進行質量提升;另一方面,數據使用者因權利無保障而不敢深度開發應用。這種“雙輸”局面直接制約了數據要素的配置效率,我國數據要素的流通效率和價值轉化率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。破解這一困局,亟需從法律層面明確數據所有權歸屬,構建“歸屬清晰、權責明確、保護嚴格、流轉順暢”的現代數據產權制度。
科斯定理的啟示:產權明晰如何激活數據要素價值
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·科斯在《社會成本問題》中提出的核心觀點,為破解數據產權困境提供了理論鑰匙。科斯定理的核心要義包括兩點:其一,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,無論初始產權如何分配,市場機制都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;其二,當交易成本為正時,初始產權的清晰界定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前提。這一理論揭示了一個樸素真理: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基礎,沒有清晰的產權界定,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,資源配置必然陷入低效。
數據要素的特殊屬性使得其交易成本遠高于傳統要素:數據的無形性導致確權成本高,可復制性增加了侵權風險,時效性要求加快了交易節奏。這些特性使得數據市場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,此時初始產權的界定就顯得尤為關鍵。如果個人數據所有權歸屬模糊,數據收集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權利義務便無法厘清,必然導致要么過度保護阻礙流通,要么保護不足引發濫用。只有明確個人對其數據的所有權,才能通過市場機制形成合理的數據價格,實現“誰貢獻、誰受益”的良性循環。
數據產權明晰不僅是激活數據要素市場的關鍵,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。一旦個人數據產權明晰,就如同1978年農村改革“土地承包到戶”一樣,將極大地激活廣大群眾參與數字經濟的熱情。當民眾真正掌握了數據的主動權,他們將積極在依法依規保護隱私權的前提下,讓個人數據、家庭數據和企業數據參與交易,從而為自身、家庭和企業創造財富 。這種模式將促使數據要素在更廣泛的群體中流通共享,縮小數字經濟發展中的貧富差距,推動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。民眾通過貢獻數據獲得收入,不僅增加了自身的經濟收益,也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形成“供得出、流得動、用得好、保安全、惠民生”的全民參與、共享數字經濟紅利的良好局面。
巴西在個人數據產權市場化方面的實踐,為科斯定理的應用提供了生動注腳。2020年《巴西通用數據保護法》(LGPD)實施后,該國創新性地推出“個人數據錢包”制度:公民通過政府認證的數字錢包管理個人數據,企業使用數據需支付報酬,用戶可自主選擇數據使用范圍和價格。這種模式的成功,正是源于明確的初始產權界定——法律明確個人對數據享有所有權,企業使用必須獲得授權并支付對價,由此降低了數據交易中的協商成本和侵權風險。
巴西經驗對我國的啟示在于:數據產權制度設計必須立足國情,在保護個人權益與促進數據流通之間找到平衡。與巴西相比,我國具備三大優勢:一是制度優勢,能夠通過頂層設計統籌數據安全與發展;二是規模優勢,龐大的網民數量形成超大規模數據市場,可通過網絡效應降低交易成本;三是技術優勢,區塊鏈、隱私計算等技術為數據確權、溯源提供了技術支撐。這些優勢意味著,我國若能構建科學的個人數據產權制度,完全可能實現更高的效率與公平。
從科斯定理視角看,個人數據所有權的明確界定將產生三重效應:其一,激勵效應,公眾因能獲得數據收益而更愿意提供高質量數據,解決數據供給不足問題;其二,約束效應,企業需支付數據使用成本,倒逼其提高數據利用效率;其三,協同效應,清晰的產權降低了交易成本,促進數據在更大范圍流通融合。這三重效應共同作用,將推動數據要素從“無序占有”向“有序流通”轉變,從“壟斷收益”向“共享增值”轉型,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數實融合的樞紐:產權明晰如何賦能高質量發展
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,而數實融合正是連接兩者的關鍵紐帶。數據要素只有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,才能真正發揮“乘數效應”。但數據與實體經濟的融合,必須以清晰的產權為前提——沒有產權保護,企業不敢投入數據應用;沒有收益預期,公眾不愿參與數據共享;沒有流通規則,跨行業數據融合無從談起。數據產權制度如同數實融合的“交通規則”,只有規則明確,數據要素才能在實體經濟的“高速公路”上高效通行。
在制造業領域,產權明晰推動數據成為生產過程的“神經中樞”。有的汽車制造商在明確用戶駕駛數據所有權后,通過與車主簽訂授權協議,獲得了大量車輛的實時運行數據。基于這些數據,企業對發動機參數進行了多項優化,提升了燃油效率,節約了成本。同時,車主因授權數據使用獲得收益分成,形成“企業降本、用戶獲益”的雙贏格局。這個案例印證了一個規律:當數據產權明確后,制造業企業可以更放心地推進數字化轉型,通過數據反饋持續優化生產流程,實現從“經驗驅動”向“數據驅動”的轉變。產權制度完善的行業,智能制造普及率和生產效率相對更高。
農業領域的數據產權創新,正在重塑傳統生產模式。山東某農業合作社探索“數據入股”模式:農戶將土地墑情、作物生長等數據授權給農業科技公司使用,公司支付數據報酬,同時將數據分析結果反饋給農戶指導生產。實施后,該地區小麥畝產提高,農藥使用量減少。這種模式的核心在于,通過明確農戶的數據所有權,解決了農業數據“收集難、質量低、應用少”的問題。全國已有多個省份開展類似試點,帶動參與農戶增收,提升了數據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。
服務業的數據產權改革,催生了新業態新模式。在醫療健康領域,有的互聯網醫院通過區塊鏈技術建立個人健康數據確權平臺,患者可授權醫院使用其病歷數據進行科研,科研成果轉化后按比例獲得收益。這種模式下,醫院獲得了高質量的研究數據,患者分享了數據價值,推動了新藥研發,參與患者也獲得了收益。在金融領域,明確個人信用數據所有權后,有的消費金融公司通過付費獲取用戶授權數據,降低了壞賬率,用戶也獲得了信用數據收益。這些案例表明,產權明晰能夠打破服務業的數據壁壘,促進數據在不同主體間有序流動,催生出更高效、更普惠的服務模式。
數據產權明晰對區域協調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。我國東中西部的數據資源分布極不均衡,東部地區擁有較多的數據中心和算力資源,但中西部地區蘊含著豐富的特色產業數據。通過建立跨區域數據產權交易機制,可實現數據要素的優化配置。“東數西算”數據產權試點中,有的西部省份將當地旅游數據授權給東部企業開發,獲得了數據收益,還帶動了旅游收入增長,這種“數據飛地”模式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新路徑。
數實融合的深度與廣度,最終取決于數據產權制度的完善程度。當數據所有權、使用權、收益權的邊界清晰后,數據要素才能真正成為激活實體經濟的“催化劑”,推動產業結構升級、生產效率提升、民生福祉改善。建立完善的數據產權制度,將提升數據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,帶動數字經濟規模擴大。
從農業經濟的土地產權確立,到工業經濟的知識產權保護,每一次生產要素的產權革命都推動了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。在數字經濟時代,數據產權制度的構建將成為新一輪生產力解放的關鍵。當前,我國正處于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的關鍵期,唯有抓住產權明晰這一“牛鼻子”工程,才能破解數據流通的制度障礙,釋放數據要素的磅礴動能。
推動數據產權明晰,需要構建“法律保障、技術支撐、市場運作”三位一體的體系:在法律層面,加快制定“數據產權法”,明確個人數、企業數據、公共數據所有權的邊界;在技術層面,運用區塊鏈、隱私計算等技術建立數據確權、溯源、交易的技術支撐體系;在市場層面,培育全國統一的數據交易市場,形成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。通過這三方面的協同發力,讓數據真正成為惠及全民的“資產”,讓老百姓在數據共享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,讓企業在數據應用中提升創新能力,讓國家在數據流通中增強綜合國力。
高質量發展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體現在每一個人的獲得感、每一家企業的創新力、每一個行業的競爭力之中。當數據能夠獲得合理回報,當企業數據能夠安全流通,當公共數據能夠高效利用,數據要素就能真正成為高質量發展的“新引擎”,推動我國經濟在數字時代實現質的飛躍,為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。這場數據產權革命,既是時代的必然要求,更是我們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。
- 推薦
- 熱門